储藏室里,死一般的寂静。
手电筒的光柱在颤抖,我们四个人的呼吸声粗重得像是从另一个世界传来。真相如同一幅巨大的、由无数碎片拼接而成的壁画,在我们面前轰然展开。它没有鬼神,没有诅咒,只有被时代洪流碾碎的个体,和被刻意掩盖的集体记忆。
我感到一阵眩晕。国基楼,它不是一座鬼楼,而是一座纪念碑,一座为所有被遗忘、被抹去的人和事而建立的、无字的纪念碑。而那些传说,就是刻在碑上的、扭曲了的墓志铭。
我的目光从那些冰冷的石板和泛黄的档案上移开,扫过我的朋友们。李亭亭的眼泪已经无声地滑落,她没有去擦,只是定定地看着那份关于陈望舒的报告。林希靠在墙上,低着头,我看不清他的表情,只能看到他紧握的拳头。
然后,我的目光落在了曾天柱身上。
他站在房间的角落,身影几乎要融入黑暗。他没有看那些档案,也没有看那些石板,他的目光,一直落在我脚边的一处。我顺着他的视线,用手电筒照了过去。
那是一个不起眼的角落,堆放着一些腐朽的木板。在一块木板的缝隙里,夹着一本现代装帧的书。它在这里显得如此格格不入。我蹲下身,小心翼翼地把它抽了出来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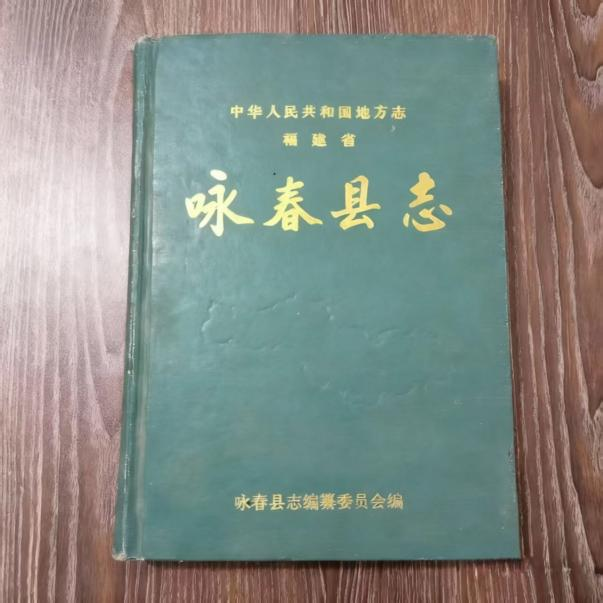
平平无奇的一本书,但看起来被翻过很多次
书的封面是《咏春县志》。我翻开书页,一股还未完全散去的、属于新纸张的油墨味扑面而来。在扉页上,有一行清秀的钢笔字迹:“历史没有真相,只有叙述。——赠天柱,二〇一四年夏。”
天柱。
我的心猛地一跳。我抬起头,手电筒的光下意识地打在了曾天柱的脸上。他没有躲闪,只是静静地看着我,那双藏在镜片后的眼睛里,翻涌着我看不懂的、复杂如海的情绪。
“天柱,这……”我举起那本书,声音干涩。
那本《咏春县志》被我捏在手里,扉页上那行“赠天柱”的字迹,在摇晃的光线下显得格外刺眼。房间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,另外两道光柱也“唰”地一下,不约而同地打在了曾天柱的身上。
他就那样站在光束的交汇点,站在我们审视的目光中,没有躲闪,也没有辩解。他只是沉默着,那副黑框眼镜的镜片上,反射着我们三个人震惊、困惑、带着一丝探究的脸。
“天柱,”李亭亭的声音最先响起,她总是最冷静的那个,但此刻,她的声音里也带上了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,“你早就知道了,对不对?从一开始,你就知道这里的一切。你带我们来,你引导我们去查档案,去找赵老师,去找泉叔……这一切,都是你安排好的。”
“为什么?”林希紧跟着质问,他的反应更加直接和情绪化,带着一丝被朋友欺骗的恼怒和不解,“你把我们当猴耍吗?你知道所有事,为什么不直接说?非要搞得这么一惊一乍的!”
曾天柱没有回答他们。他抬起头,目光穿过我和手电筒刺眼的光,看向我身后那片深沉的黑暗,仿佛在和另一个时空的自己对话。
“因为有些事,说出来是故事,”他终于开口,声音沙哑而低沉,带着一种与年龄不符的疲惫,“而亲眼看见,才是历史。”
他告诉我们,他的爷爷,是县里一个手艺很好的老石匠。上世纪九十年代初,学校对国基楼进行加固维修时,他爷爷就是施工队的一员。正是在那次施工中,他爷爷无意间打通了一面被封死的墙壁,发现了这个尘封已久的储藏室。
“我爷爷不识字,”曾天柱说,“但他敬畏亡者。他看到那些石板和档案,就知道这里面住着的,不是鬼,是一群‘可怜人’。工程结束后,他用自己的手艺,悄悄地把入口重新封好,只留了一个不起眼的活口。他叮嘱我,永远不要去打扰他们,但偶尔,要上来看看,别让屋顶漏了雨,别让虫子蛀了石板。”
就这样,一个关于“守护”的秘密,从一个不识字的老石匠,传给了一个沉默寡言的孙子。
在别的孩子都沉迷于游戏和漫画的年纪,孤独内向的曾天柱,唯一的秘密基地,就是这间装满了死亡和遗忘的储藏室。他一个人在这里,借着手电筒的光,辨认那些石板上的英文名字,翻看那些他当时还看不太懂的档案。他在这里,认识了那个爱写诗的女孩陈望舒;他在这里,知道了那个市场消失背后的无奈。他在这里,独自一人,承载了这栋楼里所有的重量。
我的脑子“轰”的一声,像是有什么东西炸开了。一个被我压抑了近二十年的、模糊而恐怖的画面,瞬间变得无比清晰。
“所以……”我的喉咙发紧,声音干涩得几乎说不出话来,“我小时候……那个停电的夏夜,在国基楼的窗外,看到的那个……哭泣的女孩背影……”
我死死地盯着他,等待着那个最后的答案。
曾天柱闭上眼睛,在那三道光束的照射下,我清晰地看到,他长长的睫毛颤抖了一下,然后,轻轻地点了点头。
那一刻,我感觉自己像是被一道闪电击中,浑身的力气都被抽空了。我踉跄着后退了半步,靠在了身后的木箱上。
原来如此。
原来是这样。
盘踞在我心中近二十年的心魔,那个关于“女鬼”的噩梦,那个让我对国基楼始终怀有隐秘恐惧的根源,在这一刻,烟消云散。那不是一个死去的女孩在哭泣,那是一个活着的、孤独的男孩,在为这满屋子无人问津的、死去的记忆而哀悼。
“我高中学了理科,但大学却转专业去了历史系……你们知道这个事吧,”曾天柱睁开眼,看着我们几个相互确认眼神后的点头回应,他的眼神里有一种卸下重负的解脱,“我读得越多,就越觉得这个房间沉重。我一个人,背不动它了。今年,我考上了郑大的博士,可能……以后就很少回来了。”
他看着我们三个,眼神里充满了恳切。
“我不能让它就这么被我一个人带走,然后彻底消失。我必须把它交给谁。我能想到的,只有你们。”他看着我,看着林希,看着李亭亭,“所以,我策划了这次‘探险’。我想让你们自己,一步步地,把这些被埋起来的东西,重新挖出来。只有这样,你们才会真正地‘记住’它。”
储藏室里再次陷入沉默。林希的愤怒和不解,早已消失无踪,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复杂的、混杂着心疼和敬佩的情绪。他走过去,重重地拍了拍曾天柱的肩膀,什么也没说,但这个动作,比任何语言都有力。
李亭亭的眼圈红了,她看着眼前这个从小就沉默寡言的朋友,仿佛第一次真正认识他。
国基楼最后的,也是最大的一个谜团,终于解开了。它不关于某个被遗忘的逝者,而关于一个孤独的、活着的守护人。
而现在,他决定不再独自守护了。这份沉甸甸的、跨越了半个多世纪的记忆,被他正式地、小心翼翼地,递到了我们面前。